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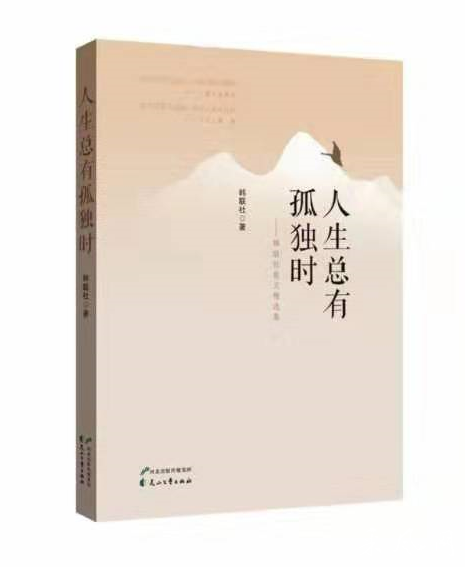
纵览韩联社近年的密集出版,“孤鹜”“孤独”的意象如此鲜醲。读完这本《人生总有孤独时》,他的整个人就立体起来了:生如夏花,死如秋叶;拥抱孤独,拒绝庸俗。
这本散文集分为上下卷。上卷的亲情篇中,父亲,继母,兄嫂,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父亲的一生,像一幅凄凉的风景画,萧瑟而寒凉。一生辛勤,一生奋斗,一生挣扎。做农民,没有力气,做父亲,又给儿女们一副多愁善感的心性,然而,最失败的,还是做丈夫……”韩联社笔下的父亲,并非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所有美德,他有时也懦弱,甚至经常对母亲冷暴力,因这,儿子们甚至希望他们早年离婚,而同样“多愁善感”的二儿子韩联社,为此还写了一封长长的《致父书》……
读着这些家事,是否想起了你的童年呢?相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大抵上都会低呼:这就是我家啊!比如我成长的家庭,庶几等于韩家的复制:只是把三男一女转换成了三女一男。一样的困窘,一样的挣扎,一样的手执书卷,却不得不面朝黄土屈服于命运的父亲。家父几乎与韩父同龄,生于1923年,曾在法国传教士的教会学校读书,后又就读于某乡间私塾,整个看上去就是一文弱书生,由于始终难逃一个农民的命运,在可怜的梦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铸就了复杂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对子女的影响却不可估量。是否可以这样说,那个特殊时期粗通文墨的父亲们,必定要把多愁善感这一特质传给子女中的某一个或几个?
在韩联社的亲情中,谁若忽略了继母这个人,他就该“恶补”博尔赫斯了。在这一点上,我与韩联社惺惺相惜——他在参加工作后才失去母亲,而我失母则是在9岁时。父亲从51岁到85岁去世,一直做鳏夫——天主教徒不允许再娶。而我也没机会让一个继母出现在生活中,所以无法预测面对一个继母时的模样。
通常,在两性关系中,当我们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把伤害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对方。在亲情中又体尝不是如此呢?有时,爱与伤害是孪生。人类就这样爱着、伤害着,一起走向清冷或温暖,殷实或空茫。于是有人提出“亲密有间”的亲情或爱情。这样的“爱且伤害”模式,不分肤色,不分人种,全世界通行,恰如眼下我正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有七个子女,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排行第二,他见证了父亲的暴力、焦躁和蛮野,同时也无可奈何地继承了父亲的古怪、多疑、忧郁和病态的敏感,读着陀氏这些描述,竟与韩联社笔下的父亲如出一辙……难道,每个作家的长成,都要经历这样的家庭环境?
韩联社笔下的兄嫂,也可圈可点。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子女成群,俗语里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何尝不是兄弟姐妹之间的隐喻?贫困使得所有人际之间窘状百出,长嫂往往与下面的小叔小姑不睦,这在那个特殊时期极为普遍。但联社兄笔下的兄嫂,却温情至极、励志至极。他们是真正的长兄长嫂,兄长尝试了修表、修电视、开出租等多种谋生手段,最后积劳成疾,撒手西归;最令人动容的,还是长嫂在众兄妹中的“母亲”位置,当父母先后逝去,嫂子深情地对弟妹们说:爹娘虽不在了,但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要常回来看看。果然,当小妹在省城工作后要生孩子了,她第一个想到的竟是嫂子,她对联社兄说:哥,你把咱嫂子接来吧……联社兄把那支《嫂子》献给长嫂,同时也触发了读者的泪腺。
更为巧合的是,我与联社兄笔下的这位小妹,竟有着非同寻常的交集。其实,多年间,我并未见过现实生活中的韩兄,只是远远地关注着这位省城的媒体达人。博客方兴未艾时,我尚醉心于体制内的一方讲台,虽时而手痒难耐暗自涂鸦,终不成气候,难以与联社兄为首的各种博客圈热火朝天的线下活动“接轨”,只有临渊羡渔的份儿。后来因各种原因,属于我的讲台渐渐缩水,这才重拾笔墨。关注到联社兄著述频出,羡慕嫉妒着,直到有一次,随省城一位公益达人去元氏县参加公益活动,同车里竟有联社兄。
这一见非同小可,作为藁城的媳妇,原来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当他听说我曾在棉纺厂工作,于是提起他的小妹宝钗,我几乎惊呼起来:我与宝钗不但同龄,还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我比宝钗高一届),并先后分配到原国棉四厂,住在单身公寓的同一层……当年,宝钗见我业余偷偷写些小稿发在当地报纸上,有一天兴冲冲地把一摞稿纸拿给我,那时打印稿还很少,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蓝色钢笔字,宝钗告诉我,这是她在报社工作的哥哥写的小说。封面上方写着五个大大的字:《都市的忧郁》。文稿没有署名,只说她哥哥是记者,对于见短识浅的我,瞬间被镇住了。惊呼身边竟有如此高人的同时,近才情怯吧,有心结识,终因自卑而懦懦。加之我很快就调离,为了适应新环境,阅读写作就弃之脑后了。这些年中,联社兄的名字如雷贯耳,却从未想到他竟是那位作者。这部中篇小说,后来收入了他的小说集《清明前后》。
在上卷中,伴随着亲情友情的,还有无边的苦难,联社兄主要抒写的是故乡老百姓的艰难生活。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也时而咀嚼着作家的苦难书写。对苦难的关注,无疑成为作家的良心课。如果在作家中寻找一个苦难代表,陀氏肯定首当其冲。显然,陀氏笔下的苦难,离我们尚远,隔了种族、家国、环境、年代,而联社兄笔下的苦难,离我们并不远,《兰芝堂姐》《文法堂哥》《勤英表姐》诸篇记述的那个年代的苦涩现实,哪怕8090后们,只要有心,都能从各种媒体或口口相传中窥知一二。
文学人注定相遇。读了本书的下卷,不由一声惊呼:联社兄在在做记者编辑的同时,从未中断写作。他的文字中,渗透出一种浓郁的人文关怀。一边做着媒体人,一边著书立说,偶一回头,竟著作等身了:《家园里的流浪》《孤鹜已远》《清明前后》《我为峰》《历史的忠告》《史海撷英录》……这些已出版的文集中,有散文随笔、传记、小说,而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也是信手拈来。除了自己的写作,他还热心于对文友的提点与擢升,特别是那些深邃而清冷的人文思考,令人回味。无论写他的老师、同学、同事,以及工作生活中的至交,无不透露出一个媒体工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眼前整个世界的人性审判,读着就有了一些鲁迅先生的味道——鲁迅也有一个名篇《孤独者》:他与乡党魏连殳同在S城谋生,二人同在月亮与六便士之间挣扎着;包括《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弟兄》中的秦益堂、张沛君……《故事新编》中,更是对《奔月》中的后羿和嫦娥,《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尽显人在梦想与现实矛盾中的苦痛拉锯。
人生识字忧患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工作,一路走来的联社兄,也经历着肉身与灵魂的拷问,凭着一双无邪的眼睛,观望着这个纷繁的世界,一颗聪慧的心,感悟、思考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并试图在粗野的世相之下,发掘出人们心灵中那些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情感。这个面色忧郁而心如烈火的文学青年、中年,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将自己的精神生活与当下的文学活动高度融汇。
背叛、挣扎、利欲,尽管联社兄经历了世事的风吹雨打,却必须承认,在这部书中,一颗纯挚之心跃然纸上。纯真、纯情、纯洁,是配得上联社兄的。以清澈之眼,观罪恶之事——这该是何等境界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到底是要讨好读者,还是要表达自己?或许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答案当然是后者。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做到后者谈何容易?稍不注意,就形成了自己的人格分裂。读着联社兄的书,毫无疑问,我也读出了他的挣扎,他的彷徨,甚至他的低落,但同时其真诚和坦率,又像咱们的“东风快递”般畅快淋漓。此刻,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
值得指出的是,读联社兄的书,有时我怀疑他是拿了中文、历史双学位。尽管人人都懂得“文史不分家”,但真正对历史如此的昵近,并从历史波澜中压榨、过虑,使之凝结成一颗颗思想的结晶,这也是我从联社兄的文字中读出一些鲁迅和李国文的味道的真正原因,以及本书序言作者刘江滨所言的“经国业”和“千古事”。显然,联社兄拒绝信号枪一样的“预备—起跑—终点”之类的固定式样,他试图通过一张键盘,探讨和开掘人生的多样性。
“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这是海明威1954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发言,却像为联社兄量身定制。海明威还说:“一个在人稠广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受孤独寂寞之苦,但他的作品却往往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非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海明威告诉我们:写作者是孤独的。难以置信,写作者从未感到过孤独。也只有在孤独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超越和灵魂自由。可否这样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孤独?然而,对于写作者,孤独却如离离原上草,总是一岁一枯荣。
读着联社兄的文字,时刻感受到他身上燃烧着一种海盗和山大王的灵魂。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击打,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叔本华说: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庸人逃避痛苦,于是他们的生命“氧化”成为一派平庸;孤独的存在,拉开了杰出与庸常的距离。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孤独来偿还。联社兄若生在古代,必是一个赍志林泉、仰天长啸的人物,大概早就携一缕风,驾一溪云,追李杜白去了。
可否,把联社兄的这些文字,统统归于孤独?——因为在我看来,它们都是孤独之子。
作者简介:刘世芬,笔名水云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国内多种报刊,著有散文随笔集《看不够的<红楼梦>,品不完的众人生》《开在刀疤上的花朵》等。
[上一篇] 乔红的妙笔
[上一篇] 读《早晨从中午开始》有感